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反行为
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反行为
我的《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(1950~1980)》终于出版了(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13.9)。“反行为”概念是我在20年前提出的,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
中国道家老子喜欢讲“一正一反”,认为一切事物之内都存在着对立物和对应行为,“反行为”从下层出发,带有一定的倾向性。但它不一定是站在哪一边,它也很少“道德预设”,从而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。读过《老子》就会知道,所谓“下”、“反”一类词汇,皆无贬义;它表示的是,任何一方若有过甚之举,便可能引起相应的反弹,一项政策设想即便是“好”的,也可能引起下层的对应行为。
如果说世间事物都处于一种“对立关系”当中,那么从中国古代老子的“一正一反”,到现代一般人所说“反抗”之间,是有层次,一步步拓展下来的,“反行为”既非前者,亦非后者,它可能就是其间一个层次的表现。
“反行为”是一种“反抗”么?或是本意“反抗”,却不得不采取的另类方式?我觉得还是应把二者区分开来。因为我们不能以“思想”而非“行为”给人“定性”、“定罪”,而且还因为,“反行为”这一层意思是太长久地为人们所忽视了。
简而言之,“反行为”是处于某种压力之下的“弱势”一方,以表面“顺从”的姿态,从下面悄悄获取一种“反制”的位势,以求弥补损失、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;它若隐若现,可以说是中国人的“拿手好戏”。
“反行为”常常被同仁理解为“反抗”,恰逢其时,国外的有关理论,如斯科特(J. Scott)的“弱者的武器”、梯利(C. Tilly)的“抗争政治”等,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。误解,或混同,更加不可避免。
到2004年我公开表示(北京大学、维也纳大学),“反行为”不是“反抗”,2010年更特别强调了这点(法国高等研究院),并把它称之为“不反之反”。现在看来,这可能是理解“反行为”的一个契入点。
易言之,“反行为”理论探讨的第一步,是把它跟“反抗”区别开来。
为什么会出现二者的混同和误解,或把一切都归结为“反抗”呢?我想,这可能是受了根深蒂固的“阶级斗争”或其他“斗争理论”的意识形态影响;同时,因为西方思想是二元的,所以都表现为这种对抗式(或排他)的理解。
“反抗”与“反行为”即使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些相似之处,如“弱者的武器”中的一些方式,特别是在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怠工、偷盗等。但据我了解,它们仍是在激烈对抗的大框架下的反应,仍然是反抗,而不是“反行为”。
“反行为”是一种微妙的人类行为,可能也不是在所有地区或所有民族都存在的。
相对而言,中国农民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通过“反抗”(例如苏联集体化时的农民的武装反抗,乌克兰大饥荒时“拉队伍”的打算等),而是通过他们的“反行为”取得的。换一句话说,中国人首先可能并不是“反”,而是“从”。是先“顺从”、“答应”了,之后再在其“顺利执行”当中,再想办法慢慢往回“找补”的。
“反行为”不是“反抗”,历史上大多数社会恐怕也并非由那种剧烈的斗争所所构成;而在统治较为严厉的地方和时期,“上面”不允许“下面”反抗什么,发现了也非镇压不可。因此,“反行为”可能正是这些社会表达不同意见所惯常采用的一种行为,也远比“反抗”使用得更为经常和普遍。
“反行为”是“下方”面对“上方”在政治上、法律上的“强势”和“尽得先机”的情势下,由“弱势者”后发的“反制”行为。它不是“反”(反叛、反抗),而首先是“接受”,如面对“集体化大风暴”,中国农民不得不先“跟上走”(与苏联很不一样),而不(也不能)作硬性抵抗。但在“服从”之后,农民就有很多办法往回“找补”,如集体化后,农民“压产”,不多产粮、交粮,多年以来维持“贡赋”在一水平线上。就此而言,“反行为”的成果大小虽“因事而异”,但它总是可期待的,有时还是很可观的。
不错,在农民的思想行为中,“反”是可能有的,它们都是集体经济的“对立物”,但未必是“反抗”。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,有时还十分微妙,在无处不在的“对立”状况之中,若想表达自己的意见,保护自己的利益,可能会出现各种“对应行为”,而不一定是“反抗”。
“反行为”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(所谓“纪律废弛”或“搭便车”,都可能造成“反行为”),即使是想“反叛”(假定有一部分人会这样想),“反抗”也不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当然,在政府眼里,则可能把它(例如“逃港”一类行为)认做“对抗”,而加以严厉打击。这里显然存在不同的视角,不能强作解人,也不应随意将自己的想法当作“历史意见”。
反过来说,世上存在一些关系,互相之间并没有到那样严厉的程度,在这种地方,恐怕也只能使用“反行为”,而非“反抗”。在清朝的宫廷和官场我们都不难发现这样的例证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反行为”就是某种“窘迫无奈”的情况下——或无法反抗,或处于并非如此对立的关系之中——所采取的一种“应对”和“反制”的行为。
“反行为”与一般“反抗”理论的最大区别,不仅在表现形式上,可能还在于“反行为”在功效上的与众不同。
“反行为”是一种日常的常规行为,未必期待一个最后的“总爆发”,却可能导致相应的后果。“反行为”由静悄悄的隐秘的日常细小行为所构成,一般而言,其效果是有限的,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或尽除下层一方的痛苦。不过,它仍可能迫使上层做出重大的制度变革和制度修订,如中国农村“包产到户”改革的实现,就有一半是被农民“拱”出来的,而无待于什么知识分子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,也不必经过什么“农民大起义”。这是“反行为”的显著特点,是与其他“反抗”,如斯科特“弱者的武器”最大的不同,亦为梯利归纳的世界各类反抗行为所不及。
从“反行为”的视角,不难看到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之间,上下相蒙,“猫腻”盛行,形成表里不一的“二相社会”,它涉及政府角色、战略定位、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,决非单一“社会冲突”所能涵盖。
《华夏时报》2013.9.9. (文字有出入)
发送好友:http://finance.sixwl.com/jingjixuejia/129054.html
更多信息请浏览:第六代财富网 www.sixwl.com
上一篇:以物品成交价作指数为锚的理想货币制
下一篇:婚姻的契约本质
·公共部门财政困难 楼继伟明确用PPP模式引民资投基建2013.09.23
·煤层气扶持开发力度将加大2013.09.23
·“天兔”来袭 粤闽多地学校停课2013.09.23
·环保部“重金”支持空气除污 征收拥堵费细则仍在研究2013.09.23
·一线城市房价登高及月 调控目标高处不胜寒2013.09.23
·8月份经济数据点评2013.09.23
 看中韩车模甜美可爱范
看中韩车模甜美可爱范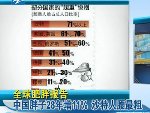 中国胖子28年增11% 沙特人腰最粗
中国胖子28年增11% 沙特人腰最粗 美艳动人 惹火豹纹女郎秀完美姿态
美艳动人 惹火豹纹女郎秀完美姿态 这20种大便你拉过多少
这20种大便你拉过多少 海南赴南沙捕捞船
海南赴南沙捕捞船 爆竹声声辞旧岁 烟
爆竹声声辞旧岁 烟 西安农民工讨薪自
西安农民工讨薪自 代表委员热议社会
代表委员热议社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