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非论“术”
刘文瑞
韩非思想的最大特色实际在术。他对法和术有明确的界定:“人主之大物,非法则术也。法者,编著之图籍,设之于官府,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术者,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,而潜御群臣者也。故法莫如显,而术不欲见。是以明主言法,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,不独满于堂。用术,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,不得满室。”(《韩非子·难三》)韩非反对管仲关于君主言论“言室满室,言堂满堂”,公之于众的做法,认为法不但要“满堂”,还要满之于整个国家,使所有人都知道,而术则不但不能“满室”,连亲近身边人都不能让其窥见。所以,韩非论术陷入了自设的困窘:一方面,君主的术要隐秘到最聪明的下属也看不到猜不透,另一方面,他又要把术说得明明白白通体透亮。这正是韩非的过人之处,同时也是他的丧命之处。
韩非之前,申不害以术知名。韩非之术,比申不害又进了一大步。术之所以要深藏不露,目的是防范臣下。在韩非眼里,他人即敌人,臣下是最危险的敌人。所有的术,都建立在君主和臣下对立的假设上。权术的起点,是假定下面会蒙蔽甚至欺骗上面。所以,绝不能相信任何人,尤其是不能相信臣下。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,信人则制于人。人臣之于其君,非有骨肉之亲也,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。故为人臣者,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,而人主怠傲处其上,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。”(《韩非子·备内》)韩非举出了大量事例告诉人们,为了权势,父子可以相残,夫妻可以反目。“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,则其馀无可信者矣。” 世界上的人没有值得信任的,术以不信任别人为前提,以不被别人蒙蔽为指向。
要使君主不被臣下蒙蔽,就要把自己的好恶藏起来而不显示给臣下。“故曰:去好去恶,群臣见素。群臣见素,则大君不蔽矣。”(《韩非子·二柄》)君主一旦表露出自己的欲望和意见,臣下就会顺着这种欲望和意见讨好君主以至操纵君主。“明君无为于上,群臣竦惧乎下”。初读史者,往往不理解为什么帝王要尽可能避免会见大臣,如秦始皇就相信“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”,所以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行踪,大臣“莫知行之所在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这不仅仅是求仙的需要,而且是帝王保持权威的需要。没有神秘也就没有权威,这一点古今中外皆同。西谚云:仆人眼里无英雄,正是此意。据说清朝高士奇不惜以金豆子为诱饵在宦官处买消息,不过是打听康熙皇帝最近在读什么书而已。所以,帝王往往把一大半心思放在算计臣下身上,连读什么书都要警惕被臣下侦察到,当然更不可能与臣下朝夕相处。然而,对臣下既要高度防范,又要用他们治国,其间的尺寸拿捏极为微妙。韩非为了说透道理,把臣下对君主的危害说得过于直白。这些理由拿到桌面上,有可能增加君臣隔阂。所以,后来的帝王即便内心信服韩非,也不得不对臣下在警惕之外包裹一层温柔和关怀的套装,用臣下之力时示以信任,控臣下之权时下以重手,“用人不疑”和“天威难测”交替使用。弄清这一点,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管理技巧十分重要。
需要指出,韩非的这种权术,不仅表现在帝王身上,也表现在各级官员乃至社会上的普通民众身上。以清朝的知县为例,他们身边的长随,作为个人上任带来的私人助手,论理应该是最为亲信之人,所以知县通常用他们来控制衙役。但长随一旦背主,对知县的伤害也最大,官员的身家性命都系于长随之手,因而其又是知县高度防范的对象。长随的行业神为钟三郎,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,借颜介之口咬定“钟三郎”是“中山狼”的谐音,由此也可见官员对长随的内心警惕。以制造臣下的恐惧心理来控制臣下,最后却会使自己陷入时时担心臣下背叛自己的恐惧之中,这是韩非之术不那么让君主惬意的地方。这种不惬意,会导致情感上更恨贰臣。中国传统中对“内奸”的惩罚往往比“外敌”更严厉,对“叛徒”的仇恨往往比“对手”更强烈,除了感情伤害的程度不同外,法家思想的上下对立假设是这种行为习惯的形成因素之一。
从上下对立出发,韩非认为,人主有五壅:“臣闭其主曰壅,臣制财利曰壅,臣擅行令曰壅,臣得行义曰壅,臣得树人曰壅。臣闭其主则主失位,臣制财利则主失德,臣擅行令则主失制,臣得行义则主失名,臣得树人则主失党。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,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。”(《韩非子·主道》)君主用术,就是要随时克服这五壅,不能让臣下蒙蔽君主,更不能让臣下控制财权(看来,古人已经有了财权“一支笔”的依据)。臣下擅自行令、做出义举,则是不能容忍的挑战。西汉立国后,相国萧何曾经为民请命,求刘邦开放上林苑闲地让民间耕种,刘邦大怒,不由分说就把这位功臣投入大牢。后来迫于大臣们的压力释放萧何,还自我解嘲说:“相国为民请苑,吾不许,我不过为桀纣主,而相国为贤相。”而萧何强卖民田,自取污名时,刘邦则很高兴,“上乃大悦。”(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)这一事例,正是韩非思想的一个验证。至于臣下结党,包揽人事,再开明的君主也难以容忍。
按照韩非的思路,臣下与君主是利益相背的。因此,臣下与君主表面上保持一致(韩非称为“同取”和“同舍”),则隐含着巨大的潜在危险。韩非断言,“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”,一竿子扫尽了全部臣下。“今人臣之所誉者,人主之所是也,此之谓同取;人臣之所毁者,人主之所非也,此之谓同舍。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,未尝闻也。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。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,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,非参验以审之也,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,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。”(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)据此,韩非断言,凡是臣下和君主一致,都是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,而借用这种信任毁誉进退他人,兜售自己主张,就是奸佞。韩非的这种思想,又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一个特色,即凡是迎合君主者,都有作奸犯科的可能性,而赞同君主却又能提出不同意见者(取舍合而相与逆者),根本不可能存在;不赞同君主而提出不同意见则为进谏,会伤害君主权威。所以,韩非的思想存在系统漏洞。一方面,民谚称“忠言逆耳利于行,良药苦口利于病”,韩非却站在君主立场上反对忠臣进谏;另一方面,奉承迎合君主就有奸佞嫌疑,韩非却又站在谋士立场上大谈“难言”和“说难”,连篇累牍谈论进言不易。批评别人言论矛盾的韩非,在他的文章中,照样用自己的矛攻击自己的盾。这是韩非术论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个大BUG。试图用打补丁来修复这一系统漏洞,只会使补丁层叠累积而降低运转效能。
君主有术,臣下照样有术。不过在韩非眼里,臣下之术只能称为“奸”。君主之术是针对臣下的,所以,用术的目的是洞察臣下之奸。韩非认为,臣下有八奸:一曰“同床”,臣下收买夫人嫔妃,“托于燕处之虞,乘醉饱之时,而求其所欲”;二曰“在旁”,身边的近习左右,察言观色,借机进谗,改变君主心意;三曰“父兄”,君主的宗室公子,与大臣串通,利用近亲关系,影响君主决策;四曰“养殃”,即“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,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”,娱其主,乱其心,从其所欲,取其私利;五曰“民萌”,即“为人臣者散公财以悦民人,行小惠以取百姓,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,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”;六曰“流行”,即辩论言说之士,“为巧文之言,流行之辞,示之以利势,惧之以患害,施属虚辞以坏其主”;七曰“威强”,即“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,养必死之士,以彰其威”,借以恐赫他人,以权谋私;八曰“四方”,即借用他国力量胁迫君主,以谋私利。“凡此八者,人臣之所以道成奸,世主所以壅劫,失其所有也,不可不察焉。”(《韩非子·八奸》)在不同的篇章中,韩非又称臣下有五奸,大体上同八奸类似,只是把宗室嫔妃排除在外。包括“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,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,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,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,有务奉下直曲、怪言伟服瑰称、以眩民耳目者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。八奸也罢,五奸也罢,均是有碍于君主权威的现象。君主用术,就是要及时察觉臣下的这些动态,把妨害君主权威的言行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君主用术,要对智能之士格外戒备。韩非提出,君主所用有七术,所察有六微。“七术:一曰众端参观,二曰必罚明威,三曰信赏尽能,四曰一听责下,五曰疑诏诡使,六曰挟知而问,七曰倒言反事。此七者,主之所用也。”(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七术》)“六微:一曰权借在下,二曰利异外借,三曰讬于似类,四曰利害有反,五曰参疑内争,六曰敌国废置。此六者,主之所察也。”(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六微》)所谓“众端参观”,是指以多种信息渠道、多个信息来源互相参验,消除门户之见,以求掌握真实情况,不被臣下蒙蔽。所谓“必罚明威”,是指严刑重罚,防止仁爱和不忍之心致乱,以救火为例,与其赏救火者,不如罚不救火的观望者更有效。所谓信赏尽能,是指赏赐力度要能激发相对人的最大努力。所谓一听责下是两词,一听是指区别愚智,如齐宣王和齐湣王听竽之不同,用来驱逐南郭先生;责下是指以事参验臣下所为,把握臣下的真实状态。所谓疑诏诡使,是指以诈术检测臣下,用计谋表达天威难测。所谓挟知而问,是指借助信息不对称显示君主的超人神通。所谓倒言反事,是指故意用错误信息诱导臣下,看其反应,察其忠奸。韩非所说的七术,只是君主权术的一部分,其关键是君主牢牢控制臣下,只要能够控制臣下,可以无所不用。七术所对应考察的六微,则是臣下背离君主控制的六种现象。所谓权借在下,就是君主大权旁落。所谓利异外借,是指君主与臣下所利不同,臣下借外国之力求其私利。所谓讬于似类,是指臣下鱼目混珠,欺瞒君主。所谓利害有反,是指君主与国家的利害,同臣下的利害存在冲突。所谓参疑内争,是指臣下手伸得太长,争权于君。所谓敌国废置,是指敌国使用反间之计废置本国有用之臣。六微之所以称为“微”,是要君主能注重微末端倪,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,祸生于肘腋之下。君主所要防范的问题集中到一点,就是臣下的僭越。
韩非所说的术,如果撇开价值判断,单纯从管理技术和统治策略角度看,其中有一些技巧性的成分是任何管理者都少不了的。然而,任何政治统治和管理技术,都存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。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,这是韩非思想的命门。目的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,更是韩非思想的缺项。后代所谓的“厚黑”,有些思路无疑来自于韩非。从历代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看,在术的具体运用上,他们很难完全拒绝韩非。但是,价值观和组织愿景的差别,使同样的术可以表现出不一样的价值趋向。例如,李世民押送犯人,令犯人回家团聚而限时返回的故事,就有术的痕迹。然而,这种术的运用出于仁慈,使其同韩非相比就有了质的变化。所以,后人往往以价值观和使命观的正当性来制约术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术的变质。民谚云: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,不害人同儒家伦理吻合,要防人则同法家思想紧扣,实际上就是儒法合流的民间表述。问题在于,利益的巨大诱惑,会不会使人们在用术时放弃道德底线?历史能够回答的是:从长时段来看,放弃道德,只讲权术,迟早会遭到反弹式报应。但是,即便从报应的角度来把握术的边界,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依然是理性算账,在逻辑上又会回归到韩非的利害计算思路。所以,韩非管理思想给后人留下的遗产,不仅仅是管理方略和技术(或者权术),而是道义和智能、伦理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认知。韩非自己也殒命于他所推崇的体制之下,这一历史悲剧的警示是:一旦管理者在为人和伦理上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而谋求上升,那么,这一底线迟早会变成自己上升的天花板。
发表于《管理学家》2012年11月
标签:韩非
上一篇:中国经济为何总患“冷热病”
下一篇:读者会愿意为博主付费吗?
·2014年秋季研究生将全部自费 收费原则上不超8000元2013.02.07
·12306瞬间无票真相抢票软件加密狗警示铁道部提升服务水2013.02.07
·2013年情人节恰逢春节长假 北京将不办理婚姻登记手续2013.02.07
·辽宁超生政协委员被免职 被爆1妻4妾6孩子2013.02.07
·2月7日深圳红岭私募主力建仓情报分析2013.02.07
·周四深圳红岭私募消息独家揭晓经典版2013.02.0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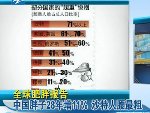 中国胖子28年增11% 沙特人腰最粗
中国胖子28年增11% 沙特人腰最粗 历史的印记 百年车模进化一览
历史的印记 百年车模进化一览 性感美艳嫩模车内激情写真
性感美艳嫩模车内激情写真 比基尼惑魅修车女郎
比基尼惑魅修车女郎 19岁混血越南瑶瑶
19岁混血越南瑶瑶 专情母虎只爱雄狮
专情母虎只爱雄狮 韩国警卫队截获21
韩国警卫队截获2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
国务院新闻办举行